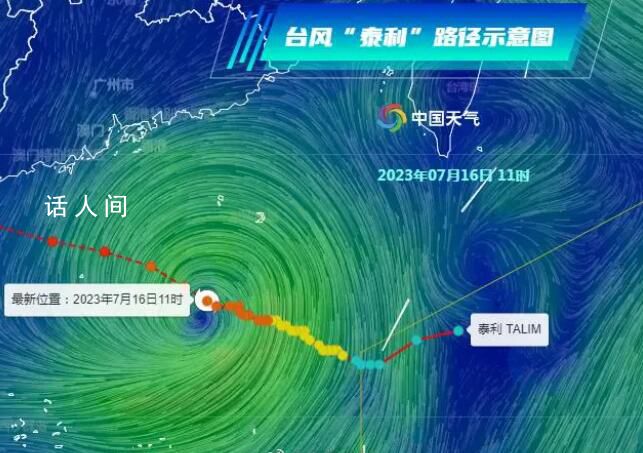洪水沖擊平原 涿州艱難六日
導(dǎo)讀:河流平靜溫順,這是三面臨水的涿州居民過去十幾年的印象。實(shí)際上,涿州的地勢相當(dāng)于一個斜坡的底部,拒馬河、大石河、小清河等多條河流從太
河流平靜溫順,這是三面臨水的涿州居民過去十幾年的印象。實(shí)際上,涿州的地勢相當(dāng)于“一個斜坡的底部”,拒馬河、大石河、小清河等多條河流從太行山脈流出后交匯于此。

和往年一樣,汛期來臨前北拒馬河的河床總裸露在外,村民們常牽著羊在河床上吃草,到了汛期,河水即使上漲,也會被河堤攔住。上了年紀(jì)的人記得1963年海河流域特大洪水,但那次水沒漫過堤壩。農(nóng)民常常為干旱憂慮。
水來的幾天前,農(nóng)民趙建國剛?cè)|馮村里交了8元的干旱補(bǔ)貼。如果今年干旱欠收,他能有一筆小小的補(bǔ)償。他家有8畝玉米田,一年能賣一萬多元。
66歲的孟祥友一直生活在涿州市北拒馬河邊。他家里種了5畝玉米田,往年田里只澆3道水,今年他特意花錢買了井水,澆了5道。6、7月下了幾場雨,他覺得“不管事”。
孟祥友記憶中,北拒馬河水量一直很少,上游放水多年,極少沒過河堤。當(dāng)?shù)厝税丫荞R河的河水深度分成“一淘、二淘、三淘”——夏季汛期之前,河水常年都是在一淘以下;上游放水后,河水一般到二淘,此時村民都愛去河里撈魚;當(dāng)河水沒過河堤時,就是三淘了。
上一次河水漲到三淘是60年前。那正是1963年,孟祥友6歲,水漫過大堤來到馬路上,人往后退一步,水就跟著走一步。他被轟著跑去前街的爺爺家住,村子里的水在不到7天后退去,而他爺爺家一點(diǎn)也沒淹著。
36歲的羅新福記得1996年有場大雨,讓他老家北辛莊戶村附近的河流還像條河流,之后便越來越干。那年下完雨,冬天一個大土坑里的水結(jié)了冰,孩子們能看見冰面下游的魚。“我們沒有任何人覺得那條河是危險的。”
7月25日,雨下起來了。孟祥友和村子里的人仍然覺得一切如常,他念叨著,到時候了,與往年一樣“上面估計(jì)要放水了”。
30日晚上,蓮池村的村干部在村里的大喇叭喊,讓村民們轉(zhuǎn)移。孟祥友不覺得需要轉(zhuǎn)移。
7月31日早上8點(diǎn),他去河堤邊上看了看,水還沒漲滿河堤,他想,又擋住了一天。孟祥友的兩個兒子勸他走。他固執(zhí)地不走,氣得兒子對父親說出了臟話。
等涿州災(zāi)情兇猛顯現(xiàn),更多的人了解到,涿州位于太行山山洪沖積扇,從太行山到涿州市區(qū),30公里內(nèi)海拔從1500米急劇下降到20米,因而水流迅猛;而且涿州又位于拒馬河、大石河、小清河的交匯處,面臨同時到來的多個洪峰。
對孟祥友而言,這地理?xiàng)l件意味著,僅僅三個小時后,拒馬河的河水就沒過了河堤,他的家和玉米田都在洪水之下了。
孟祥友看到胡同里的水時,和大兒子開了車往地勢更高的一戶三層樓去。還沒等車開到,水就從小腿肚漲到了腰。父子兩個人棄了車,蹚水倉皇而行。
他們懵然地走著,不知走了多久,遇到了救援的軍人,他們拉住了父子的手。
也是7月31日,涿州東馮村被洪水淹沒的幾小時前,農(nóng)民趙建國家里正在商量要不要撤離。
80歲的奶奶決定不走。老人經(jīng)歷過1963年的涿州水災(zāi)。那次沒淹到村里,奶奶認(rèn)為這次也沒事,不用走。趙建國支持奶奶。他想,就算水來了,“去‘敞’那里就沒事了”。“敞”就在他家窗外,那是村里最高的一塊地,寬敞、平坦,村里人都在“敞”上曬玉米。
羅新福在7月30日收到了村里的通知提示,7月28日到8月1日水量大,“別去橋邊,注意安全”。一天后,河水就漫進(jìn)了村子?xùn)|邊的京白路段。中午,他給住在村東的母親和奶奶打電話,讓她們趕緊撤離。
羅新福的奶奶說,“我活這么大了,沒見過水能進(jìn)村,不出,不出。”母親也不愿離開,敷衍他“一會兒該睡覺了”。當(dāng)晚18點(diǎn)后,他和母親、奶奶失去聯(lián)系。
想喝水的女士游出小區(qū),饑餓的居民互相幫助
走到一些低洼處,孟祥友發(fā)現(xiàn)自己腳已經(jīng)不能著地。走了不到半小時,水就漲到了胸口。一行的矮個子女人差點(diǎn)喝了口水,一個男人在水中丟了鞋子,只能光著腳走。
幾個人經(jīng)過幾處落腳點(diǎn),都沒看到救援的船只,最后爬上了那棟三層樓的樓頂,孟祥友從水里出來時,“凍得嘚嘚的”,等待了3個多小時,同行的人一直在打電話,但始終沒有信號。
他們看到救援船從遠(yuǎn)到近一艘艘路過,孟祥友和村民們招手、呼喊,聲音被水聲淹沒,沒有一艘船為他們停下,最后,他們等到了同村人的船。
當(dāng)晚18點(diǎn),羅新福跟母親最后一次通話時,母親說,村里進(jìn)水了,自來水和燃?xì)舛纪A耍戌P車幫忙轉(zhuǎn)移,之后手機(jī)無法撥通。
羅新福不斷在網(wǎng)上刷信息,一些村子已經(jīng)斷水?dāng)嚯姅嘈盘枺俏饕粋€村子的村民都站到了二層樓的房頂上。許多圖書倉庫被淹了,書本漂在污水里。他想知道自己村莊的情況。
70歲的楊新成家住在豆各村堤壩旁邊。31日,他在窗前伸出手估算,洪水“只有一根手指那么深就要溢出來了”。
“這水是沿著大清河沖過來的。”他說。
他把米面等怕潮的糧食放到屋里高處,向10公里外的何各莊撤離,那里有幾棟新蓋的高樓。可到了那也不安全,楊新成在何各莊再次被水圍困,兩天后才被救出。
趙建國的母親在抖音上刷到了碼頭村被淹的視頻,感到害怕,堅(jiān)持要走。一家人最終在來不及之前,收拾行囊,來到村長通知的安置點(diǎn),一所距離東馮村20里地的學(xué)校。
校舍有四層高,趙建國感到安全。直到第二天,學(xué)校里灌進(jìn)了水,水沿著臺階一級一級往上漲,淹到二層。
8月1日,陳天強(qiáng)正在小區(qū)一樓的便利店里碼貨,看著水破門而入,他再往高處碼貨也來不及了,只能蹚水逃回了家中。看著樓下的水越來越高,他和朋友兩人游泳回到了便利店,撈回來多箱水、方便面,放到了單元樓梯間,分給鄰居們。他后來在九樓的朋友家中困了4天。
在救援隊(duì)到來之前,家住在范陽橋西某小區(qū)的一名女士,從小區(qū)里翻越重重障礙游了出來——因?yàn)樗牒人?/p>
小區(qū)北側(cè)最深處達(dá)到了兩米。她所在單元樓靠南,水剛好齊腰。因?yàn)橄牒鹊剿龥Q定游出小區(qū)。一路上,她攀著各種障礙物游。出小區(qū)后,外面仍是一片汪洋。她翻過范陽橋旁邊一個村子,又翻越了村子的圍墻……最終這位勇敢的女士和丈夫匯合,喝到了水。
受困者臨時造的一艘“船”。
受困者在墻上貼出的“SOS”。
大水淹沒城區(qū)三天后,潁上藍(lán)天救援隊(duì)隊(duì)員趙鵬飛在小區(qū)間搜救時,一路上,目睹了居民逃生留下的各種痕跡。
他看到幾塊保溫板、木條黏在一起的臨時“船”,看到一家企業(yè)的樓身上貼著一張大字,寫著“SOS”。隊(duì)員們經(jīng)過時喊了一嗓子,無人回應(yīng),他暗自希望,這些人已經(jīng)被救走了。
工人睡在臨時棚房,直到洪水沖進(jìn)工地
7月20日開始,家住涿州市區(qū)、在政府單位工作的情侶高成齊、吳玲說,幾天里單位郵箱陸續(xù)收到七、八封防汛預(yù)警郵件。兩人沒在意,他們不知道“全市平均降水量350毫米”意味著什么,每年這幾天,都會收到類似通知。當(dāng)水真正灌進(jìn)小區(qū)時,高成齊剛剛下班回家5分鐘。被救出來的時候,高成齊看了眼家里的濕度計(jì):97%。
31日上午,北辛莊戶村村民發(fā)現(xiàn)停電了,村里的廣播失靈。同時,村民們的手機(jī)信號極弱,下午1點(diǎn),只有一部分人收到了村支書在微信群里的撤離通知。這個村的村民成為涿州最早一批災(zāi)民。
8月1日上午10點(diǎn)半左右,刁一村村支書在群里通知村民撤離:“家里是樓房的,馬上搬到二樓去;不是樓房的,找好街坊上他們家;實(shí)在找不著,上商業(yè)街,那兒有床可以住。”之后,村中樓房、商業(yè)街連續(xù)被淹,村民幾次撤離。
在涿州市騰飛路附近的一處建筑工地,一個有機(jī)會發(fā)出警告的施工負(fù)責(zé)人李軍,沒有完全公布他所知的消息。
工地開發(fā)商在30日告訴李軍,接下來幾天將會泄洪,泄洪可能導(dǎo)致城區(qū)積水深至3米到4米。李軍在31日向來自南方的木工們傳達(dá)時,僅僅提及將要泄洪,督促大家抓緊轉(zhuǎn)移到高樓,但未明確說泄洪可能帶來多深的積水,“有兩千多工人在工地上,說了大家就慌了,怎么搞。”他后來辯解說。
當(dāng)時,工人們繼續(xù)睡在有各自生活物品的臨時棚房,直到洪水沖進(jìn)工地,水深超過一樓。
附近另一處工地的工人是在8月1日下午兩點(diǎn),水到了門口,才聽到老板大喊,“趕緊上樓!上樓!”結(jié)果他們來不及拿上任何東西,徑直跑上了十幾樓,被困了20多個小時后,才從救援隊(duì)員手上接過來第一口吃的。
建材商人想保住他的財產(chǎn),書庫管理員不愿撤離
7月31日上午,建材商人郭艷偉開著能涉水近1米的卡車來到他在涿州碼頭村的庫房。在此之前的9點(diǎn)半,弟弟說“庫房要進(jìn)水了”,他立刻搜羅來170只沙袋裝上卡車,十幾分鐘后,開始往庫房的三道門前壘沙袋。
庫房內(nèi)堆著齊人高的木皮等共計(jì)價值數(shù)百萬的建材成品。
如果沒有洪水,大兒子那天會像平常一樣去北京上藝考補(bǔ)習(xí)班,小兒子去學(xué)英語、學(xué)畫畫,但他們當(dāng)時都在庫房,因?yàn)閹旆侩x前往北京的檢查站很近。
很快,水流變急,直接漫過剛壘好的3層沙袋。他讓妻子、孩子和大部分工人先離開。
剩下的三人改變方法,加厚沙袋層數(shù),但水流太急了。有一瞬間,郭艷偉產(chǎn)生一個念頭:用勾機(jī)挑一下泥地,改變水流的方向。但他沒那么做,“這么多水,流到別人家里也不對”。
郭艷偉身高一米七六,他瞅了一眼面前的一塊立著的木板,高約一米五。他告訴自己,水淹沒那塊板子的時候,就是他必須要走的時間。
14點(diǎn),郭艷偉和剩下的另外兩個人——他弟弟、一名同村好友,在壘沙袋將近5小時后,看到木板消失在水面下。他們準(zhǔn)備撤退。
僅僅20分鐘后,水沒到他脖子處,走到門外,三人搭著手在水流中前行,但很難邁開步子,水流迎面而來,幾乎把他們沖倒。
他們本能地調(diào)轉(zhuǎn)方向,往距離村子300多米、地勢較高的檢查站方向走。通過檢查站,就是北京。檢查站有4層高,主體穩(wěn)固。
途中,他看到管理一座書庫的鄰居孫翔還在拼命加固倉庫的門,為保住圖書不被水流沖走。郭艷偉大聲勸說對方離開,幾人手拉手涉水走到檢查站。
此刻,天仍然下著大雨。郭艷偉聯(lián)系碼頭村的村書記,書記調(diào)來的一臺鏟車在當(dāng)晚抵達(dá)。
8月4日下午,刁一村,泥水仍然達(dá)到小腿處。
孫翔和幾名員工執(zhí)著地留在了檢查站不愿走,他們放心不下庫房里價值兩千多萬元的圖書,因此沒吃沒喝地在檢查站守了兩天,想著他們的書。
“每個人要有自己的愛好,我的愛好就是救人”
穎上藍(lán)天救援隊(duì)趕到涿州的第一天傍晚,其中一個小分隊(duì)決定開著剛修補(bǔ)好的皮艇去救一名被困小區(qū)的70歲老人。居民說,她可能是小區(qū)里剩下的最后一人。
本地人楊陽擔(dān)任了小分隊(duì)向?qū)В械骄仍畢f(xié)調(diào)混亂,于是自己點(diǎn)對點(diǎn)對接救援需求,“能救一個是一個”。能坐下6人的皮艇緩緩駛進(jìn)原本是街道的河水,水漸深,空氣也顯著地由悶熱瞬間涼了下來。
小分隊(duì)隊(duì)長叫石虎,坐船頭,他感受到?jīng)鲆猓涯_伸進(jìn)水面,渾濁的水在他的腳兩邊分開。
這里是涿州的高新區(qū),街道兩邊的工廠門牌樹立。中通快遞轉(zhuǎn)運(yùn)中心的包裹不時從水面漂流過來。拐過街角,一陣刺激性氣體讓隊(duì)員們皺眉,水面上漂浮著疑似化學(xué)物質(zhì)的油狀物。
救援船只都帶著物資。
“河道”旁,一棟修建中的大樓。
被救出的居民。左:穎上藍(lán)天救援隊(duì)隊(duì)員石虎。
從救援船往遠(yuǎn)處望去,水霧遮擋了視線。
船行過半,水已經(jīng)深至3米,再往前接近4、5米。這時,遇見幾艘回程的救援船,吹過哨子,石虎聽對方喊道,“前邊又要泄洪了,趕緊走!”
即使是接受救援指揮部調(diào)遣的救援隊(duì),也對再次泄洪的消息毫不知情。小分隊(duì)只能放棄救人,掉頭回去。他們說:“明早再回來。”
穎上藍(lán)天救援隊(duì)總共有80多人,來自安徽阜陽的一個小縣城穎上。8月2日晚上10點(diǎn),隊(duì)伍的創(chuàng)建者、隊(duì)長杜輝帶隊(duì)出發(fā),他在隊(duì)內(nèi)募資3萬多元,帶著兩條橡皮艇,9名隊(duì)員做好了駐扎一個月的準(zhǔn)備。
到了現(xiàn)場,杜輝意識到這次水災(zāi)和以往他參與過的多次水災(zāi)救援的最大不同:水流大、急,不少發(fā)動機(jī)馬力不足的船無法開進(jìn)去。
杜輝帶來了30匹馬力的大發(fā)動機(jī),去一處河對岸接了6名災(zāi)民,其中一位還抱著孩子,正往回走時,迎面過來的一艘救援艇帶起了一股大浪,疊加河上的湍流,一大股水掀進(jìn)船里,船猛地往下一沉,已經(jīng)來不及用手往外淘水了,杜輝一下子加大馬力讓船抬起來,船頭壓在了浪上,水順著船的傾斜倒了出去,大人孩子們一起哭喊起來,但船保住了。
“說完全不慌是騙你的。”杜輝說。當(dāng)時他在船尾差點(diǎn)被沖走。
如果船真的要沉了,他會把救生衣脫了讓孩子穿上,這是他和隊(duì)員們在出發(fā)前就約定好的原則。救援工作涉險,隊(duì)員們沒有人身保險。
救援隊(duì)員們白天連續(xù)工作十幾個小時,餓了就啃一口餅干、方便面,晚上睡在籃球館、蹦極館里,幾名隊(duì)員睡在同一張蹦床上,有一個人翻身另外幾個都得跟著動。
救援隊(duì)們晚上睡覺的其中一處場所。
不出任務(wù)時,隊(duì)員們是做裝潢的、養(yǎng)龍蝦的、開汽修店的……做救援沒有工資和獎金,隊(duì)員們自己貼錢。杜輝2015年在廣東做不銹鋼生意,每次廣東有臺風(fēng),都會有救援隊(duì)沖到一線。他自己來自農(nóng)村,“不缺吃不缺穿以后,就想著怎么幫一幫別人。”至今他為這支隊(duì)伍投入了20萬。
“每個人要有自己的愛好,我的愛好就是救人。”杜輝說。
救援隊(duì)匯聚涿州,救援困難重重
7月29日,來自本地的涿州藍(lán)天救援隊(duì)開始集結(jié)隊(duì)伍,他們是涿州最初的救援力量之一。根據(jù)當(dāng)時情況判斷——中央氣象臺發(fā)布了京津冀等地的暴雨紅色預(yù)警——20名隊(duì)員只準(zhǔn)備了1艘船。而到了7月31日,他們增加至9艘。
31日,涿州東部的拒馬河、西部的大清河上游水庫都開始泄洪,當(dāng)天晚上涿州所有河流都進(jìn)入了防洪緊急狀態(tài)。救援困難重重。水流湍急,哪怕橡皮艇上發(fā)動機(jī)馬力開到最大,也沖不過去;信號沒了,及時聯(lián)絡(luò)十分困難,救援隊(duì)員周明開著船到了一個救援點(diǎn),才意識到船過不去,只能回到市區(qū)指揮部告訴隊(duì)長,再前往下一個水流更平緩的救援點(diǎn)。
8月1日起,各地救援隊(duì)開始趕往涿州,兩天內(nèi),12支救援隊(duì)陸續(xù)到達(dá)了市區(qū)的救援指揮部。其中一支隊(duì)伍是河北省內(nèi)的藍(lán)天救援隊(duì)。帶隊(duì)隊(duì)長王永富前一天已帶著隊(duì)員去了30多公里外的保定市淶水縣山區(qū),那里山洪暴發(fā),救援難度更大,在上級的調(diào)配下,王永富把隊(duì)伍轉(zhuǎn)移到了更能發(fā)揮作用的涿州。
1日凌晨到達(dá)涿州前,王永富聯(lián)系了涿州市應(yīng)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員,詢問辦公地點(diǎn)。對方說:“我們辦公室也被淹了,也在找辦公地點(diǎn)呢。”
涿州市救援指揮部被臨時設(shè)在了一條國道上,很快,國道也被淹了,指揮部只能再往地勢更高處轉(zhuǎn)移。
最新的指揮部地址是天外天烤鴨店。這個名字在志愿者、救援隊(duì)口中頻繁出現(xiàn)。在這家烤鴨店大堂的一個角落,手寫的“指揮部”泡沫板放在冰柜上,幾位志愿者不停打著電話,身邊堆滿礦泉水和方便面。
臨時搭建的救援隊(duì)指揮部。
救援隊(duì)尋找救援任務(wù)、修船加油等補(bǔ)給都靠微信群內(nèi)的消息,信息很難及時同步。常常出現(xiàn)救援隊(duì)到時人已經(jīng)救出來了,或者物資沒帶夠的情況。各種難辨時效的求援消息,考驗(yàn)著救援力量的判斷力。
各地來的救援隊(duì)們。
焦作斑馬救援隊(duì)隊(duì)員正在休息。
安川夫婦“變魔術(shù)”,救援隊(duì)要邀請函
安川和趙穎卸物資時,安置點(diǎn)學(xué)校的校長對著他們的房車感嘆,“像變魔術(shù)一樣,能裝這么多”。
8月3日凌晨1點(diǎn),安川、趙穎夫婦開著房車從天津抵達(dá)涿州這個安置點(diǎn)。他們一路飛馳,50箱方便面、50箱礦泉水、10箱榨菜、10箱壓縮餅干把房車塞得嚴(yán)絲合縫,只剩下駕駛室能坐下兩個人的空間。
食物以外,他們還帶了2100個大垃圾袋、1000個抵達(dá)時還熱著的燒餅、小號尿不濕、葡萄糖粉、5箱藥品和10箱84消毒液。
夫婦兩人都是天津藍(lán)天救援隊(duì)成員,2021年也一起去河南賑災(zāi)。河南一個安置點(diǎn)的人曾和他們說,他們?yōu)暮笞钚枰钠鋵?shí)是又大又厚的垃圾袋,因?yàn)榈冒寻仓命c(diǎn)的生活垃圾、洪水帶來的垃圾運(yùn)走;災(zāi)后可能有疫病,防蚊蟲的藥品也十分急需;帶葡萄糖粉則是一位醫(yī)生朋友的建議,用水一兌就好,補(bǔ)充糖分比吃飯快;帶上最小號的尿不濕是考慮到剛出生不久的嬰兒,穿不上常規(guī)型號的尿不濕。
他們開來的房車也是一種物資,只要有水灌進(jìn)去就能燒出來熱水,“想著能讓救援隊(duì)的人上來洗個澡”。
上一次去河南賑災(zāi)前,夫婦倆吃著飯,看到前方醫(yī)生朋友發(fā)過來的災(zāi)后現(xiàn)場視頻。兩人簡單討論了幾句,就放下碗筷出門買物資,開車出發(fā)了——這回也是。
他們帶了一車物資,但沒什么是供他們自己的。上車前他們在天津吃了一套煎餅果子就匆忙出發(fā),24小時以后,才吃上一塊壓縮餅干。
8月4日清晨6點(diǎn),受災(zāi)最嚴(yán)重的碼頭鎮(zhèn)、刁窩鎮(zhèn)被接管,不少地方水位下降,災(zāi)民們心態(tài)放松了一些,微信群內(nèi)要物資的需求變多,隊(duì)長杜輝等到中午也沒有救援災(zāi)民的任務(wù),于是決定接受救援10只貓的任務(wù)。
這10只貓屬于吳玲,她和男朋友在8月1日傍晚開車回家,停完車上樓的5分鐘里,洪水灌進(jìn)小區(qū)。兩人想著晚上肯定漲不到三樓,就先睡了。等他們醒來時,發(fā)現(xiàn)水已經(jīng)漲到膝蓋,兩人決定離開,坐上救援船只。
吳玲養(yǎng)了三只加菲,一只中華田園貓,一只矮腳貓,還有五只剛生下來的小貓。她曾考慮花8000元買一條船。但因?yàn)樾盘柌缓茫粫簺]回復(fù)賣家,船就賣給了別人。
當(dāng)她被抑郁癥折磨得最痛苦的時候,是這些貓給了她安慰。當(dāng)杜輝和隊(duì)員最終把七個貓包內(nèi)的10只小貓遞到了吳玲手上,她感激地接過去,白色褲管拖到污水中,也來不及卷起來。
這一天,大多數(shù)已經(jīng)抵達(dá)涿州的救援隊(duì)都接不到救援災(zāi)民的任務(wù)了,紛紛收拾裝備準(zhǔn)備離開。杜輝兩天都沒有聯(lián)系上涿州應(yīng)急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,拿不到救援的邀請函。這意味著回安徽后,缺少遞交給當(dāng)?shù)貞?yīng)急管理部門的一道手續(xù),回程高速過路費(fèi)也得自費(fèi)。
電話溝通了一整天,杜輝最終拿到了邀請函。幫忙開函的當(dāng)?shù)叵驅(qū)дf,“人家出錢又出力,最后不能一張紙都不給人家,讓人家寒了心。”安徽潁上救援隊(duì)在下午7點(diǎn)離開了涿州。
有志愿者自告奮勇,代替離開的救援隊(duì)在涿州補(bǔ)開邀請函。手續(xù)幾天內(nèi)簡化了,現(xiàn)在只要名字和救援的照片就能開。
保定藍(lán)天救援隊(duì)的王永富和隊(duì)員決定再赴保定市淶水縣。他在31日離開但一直放心不下那里的人。8月5日下午,他和隊(duì)員們向著淶水出發(fā)。
農(nóng)民失去財產(chǎn),商人守住廠房
8月3日中午,一輛從北京開到涿州的高鐵到站了。不到十歲的孩子看著窗外洪水漫過的田野。下了車,一團(tuán)水汽把人裹住,像是南方城市一般。整個涿州幾乎都被浸泡在黃色的泥水里。
碼頭村村民王木養(yǎng)了一千只鵝,大部分都死了。不是被洪水悶死,也不是餓死,而是“幾天里不停地游,直到游累了,就淹死了”。一些鵝臟了羽毛漂在水面,一只鵝的脖子垂掛在繩索上。幾只幸運(yùn)的鵝,無聲立在浮板上,這幾天也餓得瘦了。
王木為自己悲哀,也為村里的任老東悲哀。任老東的一百只羊也泡水了。
城南,嚴(yán)家的兩名不到十歲的男孩走失了,母親哭著尋找。微信群里的尋人信息很快被其他求援消息淹沒。
家住刁窩鄉(xiāng)白塔村的張樂開了家農(nóng)資用品店,如今店里全是污泥。兩天沒合眼,眼珠上布滿血絲,他的眼眶也是紅色,光著膀子和員工一起清理店面。
他預(yù)估損失約數(shù)十萬元,“對我們來說是全部了。”
有人要拍照記錄,赤膊的他要求收拾下自己,“起碼給我找件背心穿上”,又要來一把刮胡刀,迅速刮了胡子。
8月5日,涿州一家印刷廠員工王甫東去廠房清算損失時,地上還有30厘米積水。廠房仍然沒通電,他摸黑看見數(shù)百個裝著白紙的牛皮紙箱淤積在泥漿中。
王甫東估算,這個擁有近10個印刷廠的園區(qū)約有10多萬令紙被淹沒,“光是紙的損失估計(jì)三四千萬”。這些紙本來能印出上百萬本書。
少有人像建材商人王將一樣守護(hù)了自己的財產(chǎn)。他十分幸運(yùn)也十分勇敢。在意識到“這場雨會非常大”,注意到氣象局發(fā)布了暴雨紅色預(yù)警后,他出門購置了多個沙袋、兩臺抽水機(jī),接下來,這個商人在自己的廠房里守到了底。
31日,洪水來了。一天之內(nèi),廠房附近的水位漲到兩米五,幾乎所有鄰居的廠房都泡了水。水越過了王將的沙袋,進(jìn)了廠房外的院子,但24小時連續(xù)工作的兩臺抽水機(jī)讓院子內(nèi)的水位一直維持在腳脖子處,而廠房內(nèi)沒進(jìn)一點(diǎn)水。
兩天兩夜間,他守住了自己的財產(chǎn)和客戶上百萬的貨物。
收拾殘局后,更拼命地奮斗
8月5日,水淹到脖子才愿意離開廠房的建材商人郭艷偉回到原地,收拾殘局。泥濘的地板上堆放著齊人高的木皮,木皮按顏色分堆擺放,可以根據(jù)客戶喜好定制。木皮的下半截濕透了。廠房最里面的辦公室,地板傾斜,地面沉降。
他此前的拼命搶救仍然起了作用,沒有全毀。有31日在庫房的經(jīng)歷,他第二天獲救后就讓工人用沙袋加固了這處工廠。然而水壓太大了,水從門縫、甚至從地底下滲出來,吞噬郭艷偉的財產(chǎn)。
廠房在刁一村,村口往里走300米左右,門口掛著橫幅,表明了他另一個身份:涿州知識分子聯(lián)誼會非公有制經(jīng)濟(jì)人士組的理事。
郭艷偉在北京上的初中,2006年畢業(yè)后沒再讀書,跟著家具師傅學(xué)起了手藝,3個月后,他成為了老板,把師傅變成了自己員工。2008年趕上建設(shè)北京,“一下我就起來了。09年我的流水就上了700萬。我真是建設(shè)北京的一分子。”
在北京,郭艷偉最大的客戶之一是鏈家旗下的自如,項(xiàng)目包括北京婦聯(lián)的辦公樓、安貞醫(yī)院通州分院。這座小型工廠車間是他2017年建的。他的公司有27名員工,一年流水7000萬,利潤約在7%-11%。主要業(yè)務(wù)是全屋定制,從生產(chǎn)到設(shè)計(jì)都干。目前他估算,此次損失約1100萬。
8月4日下午,東馮村的趙建國坐在涿州職教中心的林蔭道路牙子上發(fā)汗。他已經(jīng)在這坐了三個小時。職教中心是涿州一處主要的災(zāi)民安置點(diǎn),趙建國的宿舍住了12個人,只有一臺電扇。他的妻子、父母和奶奶被藍(lán)天救援隊(duì)救出來后,去了親戚家。他一個人來了這里。
趙建國穿一雙黑色拖鞋,上面有青蛙卡通圖案,左手小臂拉了一道長傷口,是前天逃生時剮蹭傷的。提到洪水,他露出痛苦的表情,眼角流出眼淚來。
從小到大,他不知道自己住在泄洪區(qū)。而這次以后,他想搬家但沒有辦法。“沒地兒搬呀?也沒地兒搬。”
作為安置點(diǎn)之一的涿州職教中心,人們在林蔭大道休息交談。
小時候,羅新福的父母總嚇唬他,家附近的河里有水猴子。他害怕,沒真的下過水,但他會偷偷去河邊,那里有“特別干凈的沙灘,漂亮的貝殼”。羅新福曾經(jīng)是北漂,在鏈家當(dāng)房產(chǎn)中介。
2016年,他一時興起,去小時候的河邊看看,撿起一只貝殼,里面全是泥了。近年,回到老家發(fā)展后,他也不再覺得老家的河“是個景觀”。
羅新福的一位朋友,最近在拒馬河邊購置的新樓盤一套房剛剛交付,一層樓光裝修花了20多萬,目前全泡在水里。這個叫“中冶未來城”的開發(fā)項(xiàng)目氣勢很足,宣傳時的賣點(diǎn)是“內(nèi)置幼兒園,毗鄰拒馬河濕地公園”。
整個小區(qū)的水位一度高達(dá)4、5米。據(jù)《話人間》報道,一名業(yè)主8月2日跳入洪水中,游到小區(qū)大門處多次下潛,拔出插銷,讓救援船進(jìn)入小區(qū)。
8月2日,羅新福聯(lián)系上了母親,得知她當(dāng)天早上6點(diǎn)多坐船轉(zhuǎn)移到了安置點(diǎn)。母親在電話里頭說,家里的狗沒了。倉皇離開后,忘記把家里狗籠打開,“它看了十年家了,最后落到這么個下場”。羅新福聽著流下眼淚。
脫離危險后,一位個體經(jīng)營者坐在他被泥水損毀的辦公室說,“在碼頭村,我親眼看到那些豬、羊瞬間十幾分鐘全倒地。都是農(nóng)民們的財產(chǎn)。”
建材商人決心重新開始。本地銀行的貸款經(jīng)理回復(fù)郭艷偉,銀行愿意借170萬元。他請求他們能提高到200萬。他指揮工人用叉車把全泡爛了的板材運(yùn)出廠房,防止?jié)駳饫^續(xù)破壞幸存的材料。叉車是高價租用的。“200元,給你叉一下”,他說。
他估計(jì)自己的生意回到災(zāi)前水平至少需要三年,“慢慢東山再起”。
“人在絕望的時候,發(fā)出來的那個努力是不一樣的。”過去三年,他為公司每天付出14個小時,現(xiàn)在他下了狠心,“要每天付出20個小時”。
據(jù)保定市人民政府官方消息,截至8月5日12時,全市受災(zāi)人口110.69萬人,緊急轉(zhuǎn)移涉險群眾62.7萬人;累計(jì)報告因?yàn)?zāi)死亡10人,失聯(lián)18人;農(nóng)作物受災(zāi)面積7.9萬公頃,其中絕收面積1.61萬公頃;倒塌房屋4448間,嚴(yán)重?fù)p壞房屋7286間;水毀橋梁共計(jì)284座,農(nóng)村公路水毀里程550多公里;直接經(jīng)濟(jì)損失169.95億元。
據(jù)河北省水利廳8月3日發(fā)布預(yù)測,目前降水已結(jié)束,河道水位仍在回落,后期還有3億到4億立方米的水將過境涿州。
上一篇:地震瞬間:鴨跑狗跳貨架倒
下一篇:洪水沖積平原 涿州艱難六日
-
 攀枝花公園豹子胖成了“豹警官” 年紀(jì)大鍛煉少看起來胖體檢正常2024-03-07 21:07:32近日,四川攀枝花公園內(nèi)一只圓潤的金錢豹走紅,網(wǎng)友調(diào)侃稱胖成了豹警官,引發(fā)關(guān)注。園方回應(yīng):年紀(jì)大鍛煉少看起來胖,體檢正常。近日,攀枝
攀枝花公園豹子胖成了“豹警官” 年紀(jì)大鍛煉少看起來胖體檢正常2024-03-07 21:07:32近日,四川攀枝花公園內(nèi)一只圓潤的金錢豹走紅,網(wǎng)友調(diào)侃稱胖成了豹警官,引發(fā)關(guān)注。園方回應(yīng):年紀(jì)大鍛煉少看起來胖,體檢正常。近日,攀枝 -
 多家金店足金報價突破650元每克 黃金的價格又漲了2024-03-07 21:05:30近日,國際金價連續(xù)上漲,黃金飾品價格也一漲再漲。截至7日上午,多家品牌金店的價格足金價格已經(jīng)突破了650元 克。一覺醒來,黃金的價格又
多家金店足金報價突破650元每克 黃金的價格又漲了2024-03-07 21:05:30近日,國際金價連續(xù)上漲,黃金飾品價格也一漲再漲。截至7日上午,多家品牌金店的價格足金價格已經(jīng)突破了650元 克。一覺醒來,黃金的價格又 -
 2024福布斯中國杰出商界女性 周群飛喻麗麗上榜2024-03-07 21:03:13今日,福布斯中國發(fā)布2024杰出商界女性100榜單,這是福布斯中國第10次發(fā)布該榜單,通過這份榜單可以看到中國商業(yè)世界的女性群像。其中,上
2024福布斯中國杰出商界女性 周群飛喻麗麗上榜2024-03-07 21:03:13今日,福布斯中國發(fā)布2024杰出商界女性100榜單,這是福布斯中國第10次發(fā)布該榜單,通過這份榜單可以看到中國商業(yè)世界的女性群像。其中,上 -
 呼倫貝爾現(xiàn)“寒夜燈柱”現(xiàn)象 場面奇幻而震撼2024-03-07 20:59:026日凌晨,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(qū)夜空中出現(xiàn)寒夜燈柱現(xiàn)象。夜色中一束束光柱直沖蒼穹,場面奇幻而震撼。雖已過驚蟄,但位于中國北疆的內(nèi)蒙古呼
呼倫貝爾現(xiàn)“寒夜燈柱”現(xiàn)象 場面奇幻而震撼2024-03-07 20:59:026日凌晨,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(qū)夜空中出現(xiàn)寒夜燈柱現(xiàn)象。夜色中一束束光柱直沖蒼穹,場面奇幻而震撼。雖已過驚蟄,但位于中國北疆的內(nèi)蒙古呼 -
 蔡瀾上海餐廳菜品有異物被罰5萬 有顧客在菜品中吃出異物2024-03-07 20:55:49近日,蔡瀾上海餐廳因生產(chǎn)經(jīng)營混有異物的食品,被上海市黃浦區(qū)市場監(jiān)督管理局罰款5萬元,引發(fā)關(guān)注。據(jù)上海市市場監(jiān)督管理局網(wǎng)站近日消息,
蔡瀾上海餐廳菜品有異物被罰5萬 有顧客在菜品中吃出異物2024-03-07 20:55:49近日,蔡瀾上海餐廳因生產(chǎn)經(jīng)營混有異物的食品,被上海市黃浦區(qū)市場監(jiān)督管理局罰款5萬元,引發(fā)關(guān)注。據(jù)上海市市場監(jiān)督管理局網(wǎng)站近日消息, -
-
 北京未開放個人申領(lǐng)三代社保卡 后續(xù)將逐步啟動2024-03-07 20:51:52近期,有群眾咨詢?nèi)绾晤I(lǐng)取第三代社保卡,對此,3月7日,北京市人社局發(fā)出溫馨提示,當(dāng)前,本市第三代社保卡換發(fā)工作正在分批次進(jìn)展中。自今
北京未開放個人申領(lǐng)三代社保卡 后續(xù)將逐步啟動2024-03-07 20:51:52近期,有群眾咨詢?nèi)绾晤I(lǐng)取第三代社保卡,對此,3月7日,北京市人社局發(fā)出溫馨提示,當(dāng)前,本市第三代社保卡換發(fā)工作正在分批次進(jìn)展中。自今 -
 賈康:房地產(chǎn)不會崩盤2024-03-07 20:47:59著名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家賈康近日明確表示,我國的房地產(chǎn)市場并不會出現(xiàn)崩盤的情況,并提出在適宜時機(jī)下,應(yīng)當(dāng)逐步撤除部分行政限制性措施。賈康認(rèn)為,
賈康:房地產(chǎn)不會崩盤2024-03-07 20:47:59著名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家賈康近日明確表示,我國的房地產(chǎn)市場并不會出現(xiàn)崩盤的情況,并提出在適宜時機(jī)下,應(yīng)當(dāng)逐步撤除部分行政限制性措施。賈康認(rèn)為, -
 女性生理期不適該怎么辦?為什么我會感到特別疲倦和困乏?2024-03-07 20:46:45生理期不適該怎么辦?為什么我會感到特別疲倦和困乏?月經(jīng)不調(diào)可能會引發(fā)嚴(yán)重疾病嗎?知名專家在線互動解決你的問題。月經(jīng)是女性生殖健康晴雨
女性生理期不適該怎么辦?為什么我會感到特別疲倦和困乏?2024-03-07 20:46:45生理期不適該怎么辦?為什么我會感到特別疲倦和困乏?月經(jīng)不調(diào)可能會引發(fā)嚴(yán)重疾病嗎?知名專家在線互動解決你的問題。月經(jīng)是女性生殖健康晴雨 -
 青海玉樹州雜多縣發(fā)生5.5級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2024-03-07 20:42:04據(jù)中國地震臺網(wǎng)正式測定,3月7日18時6分在青海玉樹州雜多縣發(fā)生5 5級地震,震源深度10公里,震中位于北緯33 58度,東經(jīng)93 01度。震中5公里
青海玉樹州雜多縣發(fā)生5.5級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2024-03-07 20:42:04據(jù)中國地震臺網(wǎng)正式測定,3月7日18時6分在青海玉樹州雜多縣發(fā)生5 5級地震,震源深度10公里,震中位于北緯33 58度,東經(jīng)93 01度。震中5公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