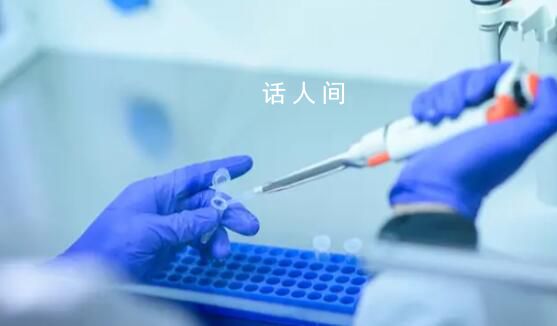天才翻譯家金曉宇近況 金曉宇最新消息
導(dǎo)讀:金曉宇的日常生活有條不紊,像一張嚴(yán)格執(zhí)行的表格。 每天不到6點(diǎn),金曉宇起床洗漱,熱飯。7點(diǎn)他步行一個(gè)小時(shí),去離家三站路遠(yuǎn)的市場買菜,
金曉宇的日常生活有條不紊,像一張嚴(yán)格執(zhí)行的“表格”。 每天不到6點(diǎn),金曉宇起床洗漱,熱飯。7點(diǎn)他步行一個(gè)小時(shí),去離家三站路遠(yuǎn)的市場買菜,再乘公交車返回。到家先洗菜,9點(diǎn)到10點(diǎn)半回臥室,開啟他固定的翻譯時(shí)間。父親離世后,“表格”里的做飯日程被提前了半個(gè)小時(shí)。上午10點(diǎn)半,他舀半杯米煮飯。吃完飯,他會聽半個(gè)小時(shí)廣播,再午休半小時(shí),接下來又到了雷打不動的翻譯時(shí)間。下午5點(diǎn)半熱剩飯,最晚晚上8點(diǎn)前洗澡上床,聽半個(gè)小時(shí)廣播就睡了。

這是50多年來,金曉宇第一次獨(dú)自生活在這間60平方米小房子里的真實(shí)寫照。在母親離世不到兩年的時(shí)間里,今年1月18日,金曉宇父親也因病去世。金曉宇開始學(xué)做菜,把米袋按照日期順序排成一列,他計(jì)算菜錢、稿酬,靠著這樣的生活細(xì)節(jié)一點(diǎn)一點(diǎn)填補(bǔ)爸爸離世之后的心理落差。
他形容自己像“苦行僧”,年輕時(shí)的命運(yùn)多舛令他固步自封。兩年前,父親的一篇《我的天才兒子》將他“推出門外”,打開了他和世界的接口,受到關(guān)注的他開始不斷得到外界的認(rèn)可。獨(dú)自生活的100多天里,這一次,由他“主動走出門外”。
“少年”心性
已經(jīng)50多歲的金曉宇,幾乎沒有白發(fā),皮膚白皙,像30多歲的青年。他說話的方式、語調(diào),青澀的微表情,更像一個(gè)不諳世事的少年。記者進(jìn)門不久,他從廚房端著一盤楊梅過來,一會兒又拿出三支巧克力味的冰淇淋——他像小孩子一樣,把自己愛吃的東西拿出來分享。
他對身邊的事物也有著少年心性般的獨(dú)特理解和規(guī)矩,不允許別人隨意入侵、打破,這種固執(zhí)是他內(nèi)心秩序的一種體現(xiàn)。
比如按部就班的日常作息,用完電腦后必須搬開桌子,將鍵盤、鼠標(biāo)歸還原位。還比如,他覺得近期自己左眼視力有所下降,他認(rèn)為跟吃了某種治療躁郁癥的藥物“準(zhǔn)脫不了干系”。
從上午10點(diǎn)開始,窩在沙發(fā)上的金曉宇來回搓手,就吃藥問題和社區(qū)黃書記展開了半個(gè)小時(shí)的辯論。“要不你減半顆?”極力勸說無果,黃書記妥協(xié)了,她深知精神疾病患者停藥的后果,遂向他分析導(dǎo)致視力模糊的多種可能。
“還是不行,吃壞了,眼睛就恢復(fù)不了了。”金曉宇重復(fù)這句話,將藥物說明中可能導(dǎo)致“視力模糊”一欄翻開給大家看。“以前我看文檔擴(kuò)大到百分之193就可以了,現(xiàn)在要擴(kuò)大到200多才能看清。”
此事最終在詢問醫(yī)生后才作罷。金曉宇答應(yīng)不減藥量,黃書記不忘囑托社區(qū)的阿德師傅一日三次給金曉宇滴眼藥水,以緩解視力問題。
金曉宇十分珍視自己的眼睛,這是他翻譯的“窗戶”。只是金曉宇一開始不知道,一只眼睛沒有了,會像天平空了一端,徹底打翻了他生活的平衡。
金曉宇6歲那年,玩具手槍里射出的一根針,正中他的右眼,不得已做了晶狀體摘除手術(shù)。小時(shí)候他不敢去做廣播體操,因?yàn)楦改父嬖V他,一旦運(yùn)動出現(xiàn)問題,需要摘除眼睛,這對外觀影響就大了。
此后,金曉宇便靠著一只眼睛生活,過得小心翼翼,原本成績優(yōu)異的他也因?yàn)橐暳栴}開始厭學(xué)。高中時(shí),他又患上了像“鐘擺”一樣搖擺不定的疾病——“雙相情感障礙”(躁郁癥)。這病后來導(dǎo)致他輟學(xué),往后每年都會住院兩三次。
母親曹女士總是在金曉宇成長的關(guān)鍵時(shí)刻做出重要的決定。比如在1993年購置電腦,讓曉宇學(xué)習(xí)上網(wǎng),而后安排自學(xué)考試,讓金曉宇去浙江圖書館借閱書籍,曉宇在六年的時(shí)間,自學(xué)了德、日、英語。又因?yàn)槟赣H答應(yīng)校友的邀請,讓金曉宇開啟了人生的翻譯之路:一部外文短篇小說《船熱》。
“目前來看,如果沒有這些東西,我的生活肯定與現(xiàn)在不一樣了。”金曉宇的父親金性勇曾打趣曹女士是“曹操后代,是家里的戰(zhàn)略規(guī)劃家”。“我爸爸表面上與她發(fā)生爭執(zhí),但實(shí)際上大事都由媽媽決策,我爸親自實(shí)施。如果沒有這些,我想象不出來現(xiàn)在到底會是什么樣子。”金曉宇說。
“死亡”與“獨(dú)行”課題
1月18日,父親金性勇因病去世。今年3月,金曉宇經(jīng)歷了最久的一次住院。
金性勇離世前半個(gè)月,都有金曉宇陪在身邊,金曉宇每天吃完中飯后,就會趕回醫(yī)院陪伴父親。父親走后,他答應(yīng)了父親的最后一個(gè)愿望:捐獻(xiàn)遺體。其實(shí),這一開始遭到了金曉宇的激烈反對,還把父親簽字的資料撕掉了,后來金性勇背著他,又偷偷地重新填寫了一份。
父親去世沒多久,金曉宇舊病復(fù)發(fā),住院近兩個(gè)月。出院后,金曉宇找到黃書記,表達(dá)了捐獻(xiàn)遺體的意愿。實(shí)際上,捐獻(xiàn)遺體的意愿也是在向父親學(xué)習(xí)。捐獻(xiàn)遺體原本是金性勇的遺愿,他不想自己的后事拖累兒子,金曉宇也表示,必須幫助父親完成這個(gè)心愿。“如果他捐的話,我也同他一樣。”
當(dāng)天簽署遺體捐獻(xiàn)時(shí),紅十字會工作人員表示,像金曉宇這樣簽署遺體捐獻(xiàn),其意義會更大。因?yàn)榻饡杂钸€捐獻(xiàn)他的腦組織,這對于雙向情感障礙這類的精神疾病的研究意義非常大,也具有很高的價(jià)值。
母親的去世讓金曉宇第一次感受死亡帶來的沖擊,而在面臨父親去世時(shí),金曉宇則不得不直面往后一人獨(dú)行的課題。相較于打擊和無措,金曉宇認(rèn)為“更多地促成了一種深層次的生活動力”。
“我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50多歲,而我爸爸是86歲去世的。如果我能活到他的年齡,即使只能再活三十幾年,也倒無所謂了。 ”
金曉宇一開始也沉浸在失去親人的痛苦中。“我想還是逐漸擺脫一些,總是沉浸在其中并不好,想他也沒有用。”金曉宇說,就像母親離開后,父親很快就處理掉了很多母親的衣服。金曉宇說舍不得丟,爸爸告訴他,有些事情不要沉浸在其中,而是要積極前行。
父親還曾告訴金曉宇,過去的事情已經(jīng)過去了,不要過多地提及困難的事情,只要是自己認(rèn)為對的,去做就行了。
這在金曉宇看來,是一種難得的心態(tài)平衡,“所以爸爸會比較長壽”。金曉宇的結(jié)論讓黃書記笑了,金曉宇偶爾蹦出來的幽默,給這間沉悶的屋子透進(jìn)一些光亮。
曉宇接著說出緣由,他想到年輕時(shí)眼睛受傷后沒有學(xué)習(xí)和工作的那段灰色時(shí)光,他連著好幾天不吃飯,對身體健康造成一定損害。“所以我不一定能活到他(爸爸)這個(gè)年齡的。”他笑了一下,笑容又很快消散。
金曉宇擔(dān)心年紀(jì)較大的人可能患有高血壓和腎衰竭,他總是擔(dān)心現(xiàn)在的時(shí)間不夠用了。“如果時(shí)間過去,后悔也來不及了。現(xiàn)在條件好了,找到竅門的年輕人學(xué)外語更快,學(xué)習(xí)時(shí)間較短。所以,除了翻譯外,只要有機(jī)會,我還是要繼續(xù)努力學(xué)習(xí)西班牙語。”金曉宇說。
一方面是學(xué)習(xí)新語言讓金曉宇翹首以待,另一方面是表哥、堂哥、社區(qū)書記經(jīng)常看望他,讓他有所依靠。他把米袋按照日期順序排成一列,“我的目標(biāo)是,家里的7袋米,每袋六七十斤,我想把這些米先吃完了。”
翻譯“苦行僧”與“天才”譯者
穿過客廳左轉(zhuǎn),靠近大門一側(cè)的臥室就是金曉宇的房間。房間不大,右側(cè)挨著窗戶放著一張單人床,左側(cè)是他的電腦桌和書架。書架上堆滿了字典、曾經(jīng)就讀計(jì)算機(jī)專業(yè)時(shí)的相關(guān)書本,以及他翻譯的原作品集。
金曉宇的第一本譯作《船熱》是由南京大學(xué)出版社推出。“除了南大,翻譯界沒人知道金曉宇是誰,社會上沒人知道我兒子到底付出了多少心血,更沒人知道這些書是一個(gè)躁郁癥患者翻譯的。”2022年1月17日,譯者金曉宇父親金性勇在這篇名為《我的天才兒子》的自述中寫到。
金曉宇形容自己的生活像苦行僧一樣。他記得在翻譯《本雅明書信集》時(shí),準(zhǔn)備了一本厚達(dá)800多頁的德漢小詞典。他每天早上背一頁,復(fù)習(xí)6頁,光背單詞就需要一個(gè)小時(shí)左右。他背了兩年多,邊提高詞匯量邊翻譯,等詞典背完了,這本書也翻譯完了。
一直對著臺式電腦,脖子、背和眼睛痛得難受,金曉宇放松自己的方式就是“乘公交”。他有一張免費(fèi)的公交乘車卡,他不設(shè)定目的地,車子把他載到哪了,他感興趣就會下車游玩。“有時(shí)乘坐公交車的一路上,感覺車窗外就像古代的山水畫一樣。”金曉宇說。
或許金性勇也沒想到,那篇自述激起的巨大反響,金曉宇被外界看到后,加入浙江作協(xié)和翻譯出版社,金曉宇的生活圈終于往外擴(kuò)大了一圈,社區(qū)還為他成立了“曉宇譯角”。5月20日,他就和省市譯協(xié)的幾位前輩們一起參與了雙蕩弄社區(qū)的迎亞運(yùn)英語學(xué)習(xí)活動,并作為社區(qū)志愿者,向鄰居們分享了自己學(xué)外語的經(jīng)驗(yàn)。
金曉宇手頭正在翻譯《印加文明》。“回來20天翻譯了40頁,馬上就可以結(jié)束了。”曉宇說,近期浙江文藝出版社郵寄的日本作家平野啟一郎的《葬送》,他還在閱讀,雙方還沒有聊合同。“我希望可以提高一點(diǎn)稿酬。”金曉宇認(rèn)為除了按字計(jì)價(jià)的費(fèi)用外,每印一本書最好可以給到他一點(diǎn)額外的收入。
“我會有一個(gè)盼頭,如果按一塊錢一本,他賣出了百萬本,我就有個(gè)盼頭。”金曉宇頓了頓,“所以說我還是比較俗的一個(gè)人。”父親去世后,經(jīng)濟(jì)方面少了一份固定收入,他不時(shí)會思考賺錢的問題,“要爭取的,我盡量爭取一點(diǎn)”。
金曉宇的主要花費(fèi)在“吃”上面。家附近的老年食堂折扣可能會便宜很多,一頓大概也要三四十塊錢。“自己做肯定便宜多了,比如說一個(gè)素菜老年食堂也要8塊多一盤,我自己做的話沒幾塊錢,還可以吃兩頓。”他計(jì)算著菜品價(jià)格,邊清點(diǎn)著冰箱里的排骨。
金曉宇會在過季時(shí)買打5折的冰淇淋,多逛幾個(gè)菜攤菜對比價(jià)格。他幾乎每頓飯都吃蝦,從未買過雞、鴨、魚肉的他曾為“花了60塊買的老鴨沒肉”而發(fā)愁,結(jié)果別人告訴他,老鴨就是肉少的,是用來燉湯的。靠著這樣的生活細(xì)節(jié)一點(diǎn)一點(diǎn)填補(bǔ)爸爸離世之后的心理落差,金曉宇的身上也慢慢沾染了些許煙火氣。
6月的一天,金曉宇收到了人民文學(xué)出版社的編輯委托人給他郵件的兩本書,希望他閱讀全文,如果覺得好,再看是否有可能給人民文學(xué)出版社翻譯這兩本書。金曉宇覺得很開心,因?yàn)楦赣H金性勇生前,視人民文學(xué)出版社為出版業(yè)的最高殿堂,如果能在人民文學(xué)出版社出版一本書,“也算是達(dá)成了他在世時(shí)對我事業(yè)上的憧憬”。
光環(huán)也好,頭銜也罷,金曉宇覺得自己因?yàn)?ldquo;天才”這個(gè)稱呼,若能被更多人發(fā)現(xiàn),也是一件好事,苦行僧的生活也開始嘗到了一絲甜。
“老貓”和“老耗子”的最后陪伴
隨著“天才譯者”被傳開,很多讀者已經(jīng)將目光投向了金曉宇的譯作。大多數(shù)人看到的,是金曉宇成名后、媒體報(bào)道中才華橫溢且命運(yùn)多舛的多語言翻譯家。
在《我的天才兒子》發(fā)出后,這間幾十平米的小房子里陷入從未有過的熱鬧氛圍。那之后的很長一段時(shí)間里,房門常常是敞開的,金性勇不厭其煩地將紛至沓來的媒體記者引進(jìn)屋,或圍坐在屋前的小涼亭,重復(fù)介紹著金曉宇在翻譯上的天賦。金曉宇則安靜待在一旁,簡單應(yīng)答。
但是社區(qū)黃書記更多看到的,是在金曉宇與躁郁癥拉扯的三十幾年里,金性勇在背后的默默承擔(dān)著這樣漫長而又日復(fù)一日照顧孩子的責(zé)任。
金曉宇每年都會犯病,有時(shí)候會出去招惹別人,金性勇總是跟在后面,向別人道歉、去認(rèn)錯(cuò)。金性勇也會請社區(qū)出面協(xié)調(diào),金曉宇又出去“惹事”,讓社區(qū)書記去跟別人說說好話,“我們道歉,愿意賠錢的”。黃書記覺得金性勇的父愛內(nèi)斂又厚重。
起初金曉宇不知道自己在情緒高亢或者壓力大時(shí),該如何尋找出口,“以前總是在家里摔東西,后來不行了,不能再摔東西了”。有一天,金曉宇覺得父母年紀(jì)大了,受不了這種壓力,“所以還是我出去避一避吧”。他拿起那張免費(fèi)的公交卡,選擇出門散散心。
在黃書記看來,金性勇父子雙方之間可能缺乏溝通,日常存在一些小矛盾。
有一次,曉宇一個(gè)人外出,沒有帶手機(jī)。金性勇告訴黃書記金曉宇走丟了,于是他們開始尋找,找了大半天都沒有找到,很是著急。直到下午4點(diǎn),金曉宇自己回來了,黃書記問他去干什么了,他說去看看墓地是否合適,他想為媽媽找一塊墓地。
爸爸很反對,父子倆大吵一架,“曉宇告訴我作為子女,他有能力去幫媽媽找一塊墓地,想把媽媽的后事做好,但是金性勇覺得這筆錢還不如省下來給曉宇。他想把錢留給曉宇,以便能過好他的日子。所以我覺得曉宇心里更多地有父母,父親心里更多的是曉宇。”
給苦難留尊嚴(yán),是出于知識分子的一種體面。金曉宇媽媽臥床的三年里,金性勇一手承擔(dān)著照顧妻子的任務(wù)。晚上每隔兩個(gè)小時(shí),金性勇就要給她翻身,所以金性勇幾乎晚上沒有睡過整覺,但白天還是要繼續(xù)做飯、洗衣、照看金曉宇。那時(shí)候黃書記曾詢問是否要幫忙找一個(gè)護(hù)工,金性勇表示不方便,自己照顧起來可能會更好。
金性勇在住院的前兩天還在做飯,金曉宇讓他請保姆,或者去養(yǎng)老院。金性勇卻不愿意,提出要花10萬元裝修房子,要給金曉宇找一個(gè)老伴。“如果他愿意,可能還能活得長一點(diǎn)。”金曉宇說。
金性勇在世時(shí),從未向黃書記提過生活上的困難,金曉宇出名后,很多人要給他捐款捐物資,金性勇一直都拒絕。他還告訴黃書記,社區(qū)如果誰有困難的,他還可以把家里的糧食拿出來幫助別人。
一天吃完餛飩,金曉宇向記者主動提及了死亡的話題。
金性勇病重住院,中途醫(yī)生說再過幾天就可以出院,金曉宇以為爸爸會沒事,“很奇怪的。”他不理解爸爸最終為何沒能出院。
父親走的那天,金曉宇毫不避諱的拍了照片,他怕以后沒了念想。可看到照片,金曉宇卻說不出來那是怎樣的感受。“一個(gè)人會悄無聲息突然離開你的生活的感覺嗎?”記者問。“嗯。”金曉宇應(yīng)答。
媽媽生肖屬虎,爸爸和金曉宇都屬鼠。早幾年,媽媽臥床后,“瘦成皮包骨”,金曉宇一直親昵的叫她“老貓”。金曉宇說,在“老貓”最后的三年多時(shí)間里,還好有兩只“老鼠”陪著她,媽媽去世后,他一個(gè)人常念叨“老貓走了,老貓走了”。
最近一年,金曉宇發(fā)覺爸爸越來越像一只“老耗子”,但他從來不敢叫爸爸“老耗子”。離別之際,金曉宇第一次摸了爸爸的腦袋,也是最后一次,“老耗子”在金曉宇的眼前一點(diǎn)一點(diǎn)消逝。
-
 攀枝花公園豹子胖成了“豹警官” 年紀(jì)大鍛煉少看起來胖體檢正常2024-03-07 21:07:32近日,四川攀枝花公園內(nèi)一只圓潤的金錢豹走紅,網(wǎng)友調(diào)侃稱胖成了豹警官,引發(fā)關(guān)注。園方回應(yīng):年紀(jì)大鍛煉少看起來胖,體檢正常。近日,攀枝
攀枝花公園豹子胖成了“豹警官” 年紀(jì)大鍛煉少看起來胖體檢正常2024-03-07 21:07:32近日,四川攀枝花公園內(nèi)一只圓潤的金錢豹走紅,網(wǎng)友調(diào)侃稱胖成了豹警官,引發(fā)關(guān)注。園方回應(yīng):年紀(jì)大鍛煉少看起來胖,體檢正常。近日,攀枝 -
 多家金店足金報(bào)價(jià)突破650元每克 黃金的價(jià)格又漲了2024-03-07 21:05:30近日,國際金價(jià)連續(xù)上漲,黃金飾品價(jià)格也一漲再漲。截至7日上午,多家品牌金店的價(jià)格足金價(jià)格已經(jīng)突破了650元 克。一覺醒來,黃金的價(jià)格又
多家金店足金報(bào)價(jià)突破650元每克 黃金的價(jià)格又漲了2024-03-07 21:05:30近日,國際金價(jià)連續(xù)上漲,黃金飾品價(jià)格也一漲再漲。截至7日上午,多家品牌金店的價(jià)格足金價(jià)格已經(jīng)突破了650元 克。一覺醒來,黃金的價(jià)格又 -
 2024福布斯中國杰出商界女性 周群飛喻麗麗上榜2024-03-07 21:03:13今日,福布斯中國發(fā)布2024杰出商界女性100榜單,這是福布斯中國第10次發(fā)布該榜單,通過這份榜單可以看到中國商業(yè)世界的女性群像。其中,上
2024福布斯中國杰出商界女性 周群飛喻麗麗上榜2024-03-07 21:03:13今日,福布斯中國發(fā)布2024杰出商界女性100榜單,這是福布斯中國第10次發(fā)布該榜單,通過這份榜單可以看到中國商業(yè)世界的女性群像。其中,上 -
 呼倫貝爾現(xiàn)“寒夜燈柱”現(xiàn)象 場面奇幻而震撼2024-03-07 20:59:026日凌晨,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(qū)夜空中出現(xiàn)寒夜燈柱現(xiàn)象。夜色中一束束光柱直沖蒼穹,場面奇幻而震撼。雖已過驚蟄,但位于中國北疆的內(nèi)蒙古呼
呼倫貝爾現(xiàn)“寒夜燈柱”現(xiàn)象 場面奇幻而震撼2024-03-07 20:59:026日凌晨,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(qū)夜空中出現(xiàn)寒夜燈柱現(xiàn)象。夜色中一束束光柱直沖蒼穹,場面奇幻而震撼。雖已過驚蟄,但位于中國北疆的內(nèi)蒙古呼 -
 蔡瀾上海餐廳菜品有異物被罰5萬 有顧客在菜品中吃出異物2024-03-07 20:55:49近日,蔡瀾上海餐廳因生產(chǎn)經(jīng)營混有異物的食品,被上海市黃浦區(qū)市場監(jiān)督管理局罰款5萬元,引發(fā)關(guān)注。據(jù)上海市市場監(jiān)督管理局網(wǎng)站近日消息,
蔡瀾上海餐廳菜品有異物被罰5萬 有顧客在菜品中吃出異物2024-03-07 20:55:49近日,蔡瀾上海餐廳因生產(chǎn)經(jīng)營混有異物的食品,被上海市黃浦區(qū)市場監(jiān)督管理局罰款5萬元,引發(fā)關(guān)注。據(jù)上海市市場監(jiān)督管理局網(wǎng)站近日消息, -
-
 北京未開放個(gè)人申領(lǐng)三代社保卡 后續(xù)將逐步啟動2024-03-07 20:51:52近期,有群眾咨詢?nèi)绾晤I(lǐng)取第三代社保卡,對此,3月7日,北京市人社局發(fā)出溫馨提示,當(dāng)前,本市第三代社保卡換發(fā)工作正在分批次進(jìn)展中。自今
北京未開放個(gè)人申領(lǐng)三代社保卡 后續(xù)將逐步啟動2024-03-07 20:51:52近期,有群眾咨詢?nèi)绾晤I(lǐng)取第三代社保卡,對此,3月7日,北京市人社局發(fā)出溫馨提示,當(dāng)前,本市第三代社保卡換發(fā)工作正在分批次進(jìn)展中。自今 -
 賈康:房地產(chǎn)不會崩盤2024-03-07 20:47:59著名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家賈康近日明確表示,我國的房地產(chǎn)市場并不會出現(xiàn)崩盤的情況,并提出在適宜時(shí)機(jī)下,應(yīng)當(dāng)逐步撤除部分行政限制性措施。賈康認(rèn)為,
賈康:房地產(chǎn)不會崩盤2024-03-07 20:47:59著名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家賈康近日明確表示,我國的房地產(chǎn)市場并不會出現(xiàn)崩盤的情況,并提出在適宜時(shí)機(jī)下,應(yīng)當(dāng)逐步撤除部分行政限制性措施。賈康認(rèn)為, -
 女性生理期不適該怎么辦?為什么我會感到特別疲倦和困乏?2024-03-07 20:46:45生理期不適該怎么辦?為什么我會感到特別疲倦和困乏?月經(jīng)不調(diào)可能會引發(fā)嚴(yán)重疾病嗎?知名專家在線互動解決你的問題。月經(jīng)是女性生殖健康晴雨
女性生理期不適該怎么辦?為什么我會感到特別疲倦和困乏?2024-03-07 20:46:45生理期不適該怎么辦?為什么我會感到特別疲倦和困乏?月經(jīng)不調(diào)可能會引發(fā)嚴(yán)重疾病嗎?知名專家在線互動解決你的問題。月經(jīng)是女性生殖健康晴雨 -
 青海玉樹州雜多縣發(fā)生5.5級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2024-03-07 20:42:04據(jù)中國地震臺網(wǎng)正式測定,3月7日18時(shí)6分在青海玉樹州雜多縣發(fā)生5 5級地震,震源深度10公里,震中位于北緯33 58度,東經(jīng)93 01度。震中5公里
青海玉樹州雜多縣發(fā)生5.5級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2024-03-07 20:42:04據(jù)中國地震臺網(wǎng)正式測定,3月7日18時(shí)6分在青海玉樹州雜多縣發(fā)生5 5級地震,震源深度10公里,震中位于北緯33 58度,東經(jīng)93 01度。震中5公里